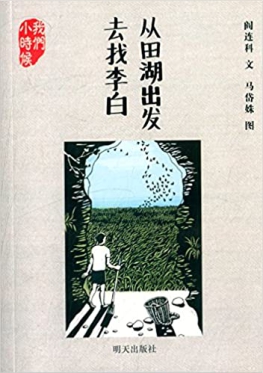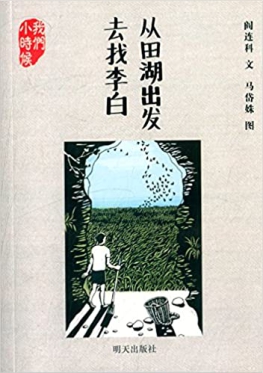
《從田湖出發去(qù)找李白(bái)》是著名作家閻連科回憶自己童年和家鄉的作品。本書(shū)寫了作者小(xiǎo)時候發生(shēng)在家鄉田湖寨的故事,既有田湖寨的曆史變遷,也有作者少年時代懵懂的感情,還有從一(yī)個少年的視角察看那個時代的社會生(shēng)活。全書(shū)語言質樸又(yòu)不乏幽默,感情細膩真摯,情感與記憶交織,字裏行間透露出作者對自己童年生(shēng)活、家鄉親人的懷念及對人生(shēng)的思考。
我(wǒ)(wǒ)要到外(wài)面的世界走走和看看。我(wǒ)(wǒ)不知(zhī)道我(wǒ)(wǒ)要去(qù)哪兒,又(yòu)好像早就計劃好了要去(qù)哪兒一(yī)樣,直到沿着大(dà)堤走離(lí)村(cūn)莊,東山漸近,田湖漸遠,一(yī)片柳林外(wài)的伊河,白(bái)花花地瀉在我(wǒ)(wǒ)面前,我(wǒ)(wǒ)才知(zhī)道我(wǒ)(wǒ)要離(lí)家去(qù)哪兒——我(wǒ)(wǒ)要獨自蹚過伊河水,爬到對面伏牛山的九臯主峰上。
老師說過,九臯是伏牛山餘脈東延的主峰,海拔九百多米,《詩經》上的“鶴鳴九臯,聲聞于天”,說的就是那山和那峰。說唐朝的李白(bái),曾獨自從龍門走來,到過那山峰,還在那兒留過一(yī)首名爲《鶴鳴九臯》的詩:
胎化呈仙質,長鳴在九臯。
排空散清唳,映日委霜毛。
萬裏思寥廓,千山望郁陶。
香凝光不見,風積韻彌高。
鳳侶攀何及,雞群思忽勞。
升天如有應,飛舞出蓬蒿。
這首詩,有啥兒意味和蘊藏,那時我(wǒ)(wǒ)是完全不懂的(現在也不懂),但覺得不懂反而好寫了,如“窗前明月光”那樣的《靜夜思》,因爲人人都懂反而寫不得。
我(wǒ)(wǒ)總以爲自己能寫出那種人人都不懂的詩,也就蓄意要爬到那山上,和李白(bái)一(yī)樣坐在山頂,詩興大(dà)發,寫出一(yī)首好到别人都看不懂的詩。當然呢,寫不寫詩不重要,重要的是我(wǒ)(wǒ)終于離(lí)家出走、獨自走了很遠的路,經曆了很多事,遇到了很多的艱辛和奇遇,它們都被我(wǒ)(wǒ)一(yī)一(yī)征服後,我(wǒ)(wǒ)成了站在山頂上的一(yī)個大(dà)人物(wù)。浪漫和草率,在我(wǒ)(wǒ)幼稚的胸膛發酵鼓脹着,使我(wǒ)(wǒ)有了一(yī)種從未有過的離(lí)家出走的英雄氣。
到了九臯山下(xià)那條“牛瞪眼”的小(xiǎo)路上。路是泥土路,可那幹硬的路面上,接連不斷嵌有突出的碎石子,好像那石子是專門鑲在地上,等人爬山時可以蹬着石子用力一(yī)樣。山在頭頂,我(wǒ)(wǒ)在山下(xià),正南(nán)的太陽燒在我(wǒ)(wǒ)的發梢上。我(wǒ)(wǒ)要站在峰頂上,讓風吹着我(wǒ)(wǒ)的頭發和衣服,環顧四周,略思片刻,最後把我(wǒ)(wǒ)的胳膊高高舉起揮動着,用我(wǒ)(wǒ)最大(dà)的嗓門兒對着天下(xià)喚:
“有一(yī)天我(wǒ)(wǒ)要吃得好也要穿得好!”
到了終于可以看清山頂時,我(wǒ)(wǒ)以爲峰頂到來了,詩也可能到來了,而我(wǒ)(wǒ)可以站下(xià)回望,首先振臂高呼口号那一(yī)刻時,卻從不遠處的山崖邊,蠕蠕動動爬上來一(yī)個人,收拾捆綁他在崖頭砍拾的柴火(huǒ)(又(yòu)是柴火(huǒ)),我(wǒ)(wǒ)們彼此一(yī)望,都怔着驚呆了。
他竟是我(wǒ)(wǒ)要躲要閃的三姑父。
三姑父就那麽如在那專門等我(wǒ)(wǒ)一(yī)樣出現了。
我(wǒ)(wǒ)呆在崖頭邊兒上,三姑父看着極吃驚的我(wǒ)(wǒ),很快平靜下(xià)來連問了我(wǒ)(wǒ)三句話(huà):
“你怎麽在這兒?”
“是你三姑讓你來這兒找我(wǒ)(wǒ)的?”
“走,我(wǒ)(wǒ)們回家吃飯去(qù)。午飯都錯過時辰了。”
我(wǒ)(wǒ)就這樣莫名其妙、前功盡棄地被我(wǒ)(wǒ)姑父強拉硬拽着回他家裏了。路上我(wǒ)(wǒ)掙着身子對他說,我(wǒ)(wǒ)是專門來爬山的,我(wǒ)(wǒ)一(yī)定要爬到山頂去(qù)。三姑父扛着柴火(huǒ),提着我(wǒ)(wǒ)的胳膊抖了抖,說山上有啥好看啊,除了野石頭就是兩棵野榆樹(shù),連花草都沒有。再進一(yī)步知(zhī)道我(wǒ)(wǒ)離(lí)開(kāi)家父母都不知(zhī)道時,他連連罵我(wǒ)(wǒ):“咋就這麽傻!”他把我(wǒ)(wǒ)拽回村(cūn)莊他家匆匆吃了飯,趕着日落和黃昏,他就帶着我(wǒ)(wǒ)下(xià)山和過河,又(yòu)把我(wǒ)(wǒ)送回田湖了。
一(yī)次盛大(dà)、莊重的離(lí)家出走行動,就這麽草草地收兵結了尾。一(yī)場人生(shēng)莊嚴的夢想與宣誓,還未來得及最後登上宣誓台,就被人從夢中(zhōng)叫醒了。現實總是比夢想有力量,少年明亮美妙的夢,被現實一(yī)碰即碎後,我(wǒ)(wǒ)這一(yī)生(shēng),再也沒有機會登上那座山,再也沒有可能在那山頂李白(bái)待過的地方坐坐與站站,高舉着胳膊大(dà)喚了。
我(wǒ)(wǒ)的少年就這樣了,還是那時候的李白(bái)好。
可我(wǒ)(wǒ)連李白(bái)的影子都沒找到,就那樣在曆史與現實的錯口和李白(bái)分(fēn)手了。